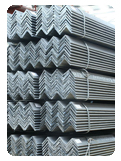夏日的暑氣總帶著幾分蠻橫,蟬鳴在濃蔭里織成密不透風的網,車間廠房被毒辣的日頭曬得發燙,連風都懶得挪動腳步。下班路過車間一角的墻邊時,眼角忽然被什么亮了一下,仔細一看發現一簇凌霄花借著老墻的筋骨攀援而上,肥厚的綠葉子層層疊疊,赭紅色的花朵綴滿了整個墻角,連磚縫里滲出來的熱氣,都被濾成了涼絲絲的綠風。
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?好像去年就種下了,一直沒什么變化,結果今春就見著了,墻根裂縫里鉆出來的細藤,嫩得能掐出水,誰也沒當回事。我走進墻角蹲下來,指尖輕觸離地面最近的那朵花,花瓣柔軟得如同姑娘的綢衫,輕輕一捻似要化在掌心,散出的芬芳甜潤得像蜜酒一般。這叢藤曾被折斷過一次,斷口處滲著黏糊糊的汁液,我心想怕活不成了,沒成想,過了倆月,竟從斷茬旁邊又鉆出三根新藤,先是纏住排水管,再順著墻縫往上繞,把巴掌大的葉子一片片攤開。等入了伏,忽然就炸開了—一串串橘紅的花,像被陽光燒紅的小鈴鐺,從濃綠里垂下來,風一吹,叮叮當當搖著,配合著高亢而嘹亮的蟬鳴聲,倒把磨機的轟鳴襯得像背景音,仿佛要將整個夏天的熱烈都傾瀉而出。
老人們說凌霄花是有性子的。它不挑水土,哪怕墻根下只有巴掌大的泥土,也能把根扎得深穩。春日里別的花爭奇斗艷時,它只是默默抽枝長葉,把藤蔓悄悄伸向高處,等到夏日最盛時,才猛然迸發出全部的生命力。那些向上攀爬的藤蔓,帶著不屈的韌勁,越過墻頭,探向鄰家的院落,甚至纏上老舊的電線桿,非要把花朵開到最高處不可。有人說它依附墻壁失了風骨,卻不知那看似柔弱的藤蔓里,藏著怎樣倔強的生命力——它從不匍匐在地,總要向著光、向著更高處生長,把最燦爛的花朵開在烈日當空的盛夏。
當夕陽西下,暑氣漸消,凌霄花更顯溫柔。夕陽的金輝灑在花瓣上,橙紅色的花朵染上一層朦朧的光暈,像一盞盞小燈籠掛在墻上。晚風吹散了白日的燥熱,藤蔓輕輕晃動,花瓣上的光斑也跟著搖曳,仿佛夕陽遺落的碎金。幾只晚歸的蜜蜂還在花蕊間流連,翅膀扇動的聲音與藤蔓的輕響交織在一起,倒比白日的蟬鳴多了幾分繾綣。凌霄花的影子纏在磚縫里,纏在舊電線上,倒像是給這道沉默的老墻,系了條會開花的綠絲帶。遠處的蟬還在叫,近處的花影輕輕晃,恍惚間,連這悶熱的夏夜,都被染上了點甜絲絲的香。
原來夏天的熱鬧,不全在荷塘和樹蔭里,墻角這點潑辣的紅與綠,憑著磚縫里那點土,憑著日頭的烤、雨水的澆,愣是把日子過成了活色生香的模樣—這大概就是夏天最野的詩意吧。只要夏日還在,待到明日朝陽升起,這充滿生命力的絢爛,便又會準時在枝蔓上綻放,年復一年,化為我們記憶里夏天最生動、最深刻的視覺符號。(大西溝礦業公司 王雪)